


羅晉
還原自然生活
私下里,羅晉性情隨和,可在戲里的淳于喬卻總愛生氣,一氣就胃疼。拍攝時,羅晉覺得淳于喬胃疼的毛病是因為工作壓力大、作息不規律,甚至是情緒引發的,“可能人不氣到那個程度,就沒法理解” 。這次,他受邀參加東方衛視跨年演唱會,秉持著“飽吹餓唱”的原則,上臺前什么都沒吃。羅晉很久沒唱歌了,猛的一來,情緒高度緊張。演出一結束,羅晉就開始胃疼,得了,他更加理解了淳于喬。
在《幕后之王》拍攝時,美術指導曾拿著一瓶香水跑到羅晉身邊說:“你聞一下這個味,你覺得你的房間是這個味嗎?”很少有美術會這么做,讓羅晉印象深刻。后來淳于喬的房間里,始終彌漫著這股味。羅晉依然保持著提前到角色的主場景(意味著大量戲份在此拍攝),的習慣,“去看這個環境”,把所有物件歸位到他認為舒服的地方,因為那樣“才更像是我的家,不用每一條都去想,自然就出來了”。
羅晉相信,角色是從生活中來的。一日收工很晚,羅晉坐的車停下等紅燈,在他的旁邊,同時有一輛公交車也停了下來。羅晉靠在玻璃上,看著公交車上那個同樣也靠在玻璃上的人。“我在想,他現在要去哪兒?他的生命中發生了什么故事?”
他也會想起讀大學時,晚上排練結束或者清早起來,和同學們去校外吃東西路過的工地,那些從工篷里進進出出的人,“端個盆出來刷牙洗臉,開心地聊著天” 。甚至出去旅行,羅晉在街上碰到玩改裝車的人,就會停下,拿簡單的英文跟人家聊上幾句。
“其實人一輩子都是在不停地抓取,不管你做哪個行業,都需要你對生活的觀察,你對人群或個體的觀察,因為都是以人為本。” 羅晉說,“就是你在過你的生活,你在看著你身邊的人和事,你從沒想過要刻意記住什么,但你觀察到的,所有令你動容的細節,都會成為你記憶中的片段。”
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故事,都是羅晉腦海中的一部電影。作為演員,他喜歡看人在不同情境下的狀態。“這個狀態是最真實的,那是演不出來的。” 如何去還原某一段狀態,這是演員羅晉所思考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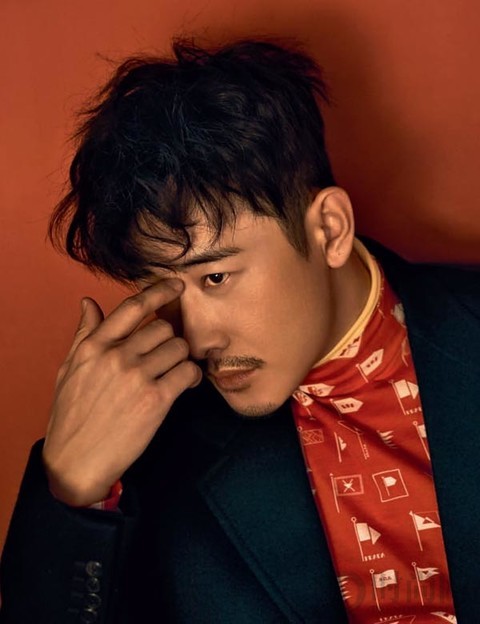
羅晉
我的釋放點在角色上
“前段時間,我一直在琢磨一個問題,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壞人?你沒有辦法去做這樣的評價。因為把好人扔在壞人堆里,這個好人就是壞人;如果把壞人扔在好人堆里,這個壞人就是好人。” 復雜的邏輯推理,羅晉一時也做不出定論。
羅晉想起2010 年《三國》中自己飾演的漢獻帝,他說自己當時想說的就是,盡管劉協作為東漢最后一任皇帝,但漢朝并非因他一人所為而滅亡。“他真的是一個努力的人,但大環境很難因為個人而改變。”后來羅晉看到觀眾的反饋中確有人看到了這一點,他覺得很滿足,“因為我想表達的,有人看到。”
同樣,隨著《幕后之王》的熱播,羅晉也收到了越來越多的觀眾反饋。“特別希望自己能夠有一個像淳于喬一樣的上司”令他印象深刻。雖說劇情設置在傳媒行業,但事實上,劇中人物所受到的職業壓力,以及面對的情感選擇,早已輻射進各行各業。“只不過它以此為切口,講了一個能夠跟很多人達成共情、產生共鳴的故事。”羅晉說,“其實說實話,我希望部分人看到這個作品,能夠對生活和工作再燃起希望。”

羅晉
《鶴唳華亭》改編自雪滿梁園的同名小說,羅晉在當中飾演太子蕭定權。盡管恪守君臣與父子之道,卻一直被父親忌憚,屢遭疏遠,不得不眼看庶長子齊王覬覦皇位。最終蕭定權為家國孤身犯險,含恨而亡。羅晉在去年接受采訪時曾提到,人類的進步需要像蕭定權這樣的人,為了純粹的信仰與熱愛行事,而這些人卻通常會被后人用“傻子”描述。羅晉認為心有堅定信念,就不會違背自己的良心。他崇拜如蕭定權這般的人,也希望自己一直做這樣的人。
事實上,羅晉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活在角色的人生里。他醒著的時間里,有十幾個小時都在片場,別人也通常會用角色的名字稱呼他。每天收工之后,“在房間靜靜地坐一會兒,把自己找回來” 是羅晉唯一可以成為自己的時刻,卻鮮少為人所知。
不拍戲的時候,羅晉始終保持著相對穩定而封閉的狀態。“只有這樣,等有一天你需要在適當的時候,缺口打開,出來的東西就會……”他找不到一個確切的形容詞,“因為生活當中我不是一個太會表露情緒的人。”快樂和痛苦、興奮與低迷都不在絕對值的兩端。
“但角色可以帶給我。”
角色帶給你什么?
“可以讓我發泄,可以讓我釋放。”

羅晉
演員能做什么
小時候,像《英雄本色》這樣的電影是需要“插錄像帶”看的,羅晉也沒看過幾部。他唯一記得的是學校組織學生看過《地道戰》《地雷戰》《鐵道游擊隊》。在家鄉,電影并不常出現在生活里。后來進了北京電影學院,同學們湊在一起討論著《七宗罪》《鵝毛筆》,羅晉說自己只能“張個嘴,睜大眼睛看著,什么都不知道”,他驚覺自己原來落了這么一大截。
起初,羅晉并沒想成為演員。若不是學了戲曲,童年的他甚至不能理解男孩子為什么要化著“胭脂妝”上臺跳舞。
北京電影學院的拉片室,是羅晉在校四年里最常去的地方。直到今天,他依舊保留著大量閱片的習慣。看得多、看得雜,不是每一部都喜歡,但時常為自己的好奇心買單。每年四大國際電影節的入圍片單一出,羅晉就開始四處搜羅喜歡的影碟,北京和上海仍舊開著的實體店鋪他都逛遍了。早前的采訪里他也透露過,自己甚至會背著投影儀進劇組。羅晉承認,在這件事上他有點兒“強迫癥”,實在一口氣看不下去的電影,分三天也得堅持看完,“看看它到底哪兒不好”。
看得多了,羅晉發現似乎所有潮流都在循環。幾天前,羅晉參加活動,他看著自己做好的頭發,回想起20 世紀80 年代流行的“一片云”發型。電影如是。早期受技術限制,電影的呈現趨近于紀錄片形式,隨著科技發展,更多技術得以應用。羅晉甚至覺得,隨著v r 技術的日趨成熟,觀影體驗或許還有其他的可能性。然而作為演員,要如何在多變的大眾化審美和市場需求中堅守自我?羅晉堅信“以人為本”。
“退一萬步說,我覺得演員這個職業其實也挺可憐的。”設想,當社會進入非常時期,演員可以做什么?“能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帶給大家一個正面的影響,而不是盲目地去崇拜,然后炫自己。我覺得演員更需要有很正的三觀,對吧?當然,每個人追求的東西不一樣,對于我個人來說,我希望做一個對社會、對身邊的人有價值的,能夠給大家帶來好的影響的演員。”

羅晉
底色
提起家鄉,羅晉說了四個字——“青山綠水”。羅晉的家鄉在江西省宜春市銅鼓縣,那兒有許多梧桐樹。到了秋天,人們會把梧桐落葉掃成一堆再點燃,空氣里都是香香的泥土和燒樹葉的氣味,“再配上晚霞,絕了”。
從小父母就跟羅晉說,做人要對得起自己做的事情,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做到自己問心無愧。不管別人怎么對自己,“我們都要以誠意、善意相待”。“其實從小家里條件還可以,所以導致我也有一個特別不在乎的心態。從A 點到B 點有一萬條路,即使這條路很難,也要想怎么把它走得漂亮,我所說的漂亮并不意味著一帆風順。”
現在羅晉時常跟劇組里年輕的演員聊天,他總感嘆“現在特別好”。羅晉跟他們說:“珍惜你們的每一段時光,珍惜你們每一階段的生活狀態,因為一旦過去了,再想回來就不可能了。” 他越發覺得生命里經過的每一個人都可能對他產生影響。他去看前輩表演,汲取優點。“看比我年輕的人演戲,有缺點也有優點,缺點要反思,優點我要不要向別人學習?” 羅晉一直是個專注的人,要怎么保持這份專注呢?“少想一點。”他說。
羅晉說,或許有一天他也會演一個“十惡不赦”的角色,“讓大家恨死我”。不在乎非議嗎?“無所謂,我是演員,我要有盡可能多的嘗試。我是順著命走的人。”羅晉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