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堯
終其一生追尋誰(shuí)
在黃堯的眼中,《白塔之光》毫無(wú)懸念地代表了一種刻入骨髓的孤獨(dú)。
謙和過(guò)于客氣的寫詩(shī)中年男人、既是自媒體博主也是獨(dú)身一人的美食家、從福利院走出來(lái)的孤兒攝影師......在跳海酒吧微醺之后吐露自己真名、抽煙、娓娓道來(lái)自己的故鄉(xiāng)......電影中這些出場(chǎng)的人物和行徑,在經(jīng)歷了冗長(zhǎng)平靜歲月之后,再次勾起我們每一個(gè)城市中或漂泊或追尋的人對(duì)于內(nèi)心塵封的執(zhí)念。
對(duì)于黃堯來(lái)講,歐陽(yáng)文慧給她帶來(lái)最大的共鳴,只是一種漂泊感。她們同樣在北京生活了一些年頭,但始終也沒能在這座城市找到一份歸屬感。因?yàn)榘职謰寢尪际潜狈饺耍依镒霾说目谖镀狈健⒓依镎f(shuō)的也是說(shuō)普通話,給還是孩童的黃堯根深蒂固地留下一個(gè)「自己就是北方人」的印象,覺得那里才是自己的家鄉(xiāng)。加之后來(lái)讀書生活在廣東這個(gè)城市,自己身上的氣質(zhì)似乎與身邊地道的南方同學(xué)有著天囊之別,屬于北方這個(gè)自我認(rèn)知愈加強(qiáng)烈。

黃堯
直到來(lái)到這里才發(fā)現(xiàn)「北京」并不意味著北方。北方對(duì)與黃堯來(lái)說(shuō)更多是意味著老家,一直就是親戚們家里,家的親切感覺;在北京要一個(gè)人生活,反而會(huì)更感覺比起家,需要更多的是堅(jiān)強(qiáng),北京讓習(xí)慣了輾轉(zhuǎn)的黃堯覺得自己是一個(gè)真正的大人,也更多需要習(xí)慣「追逐」,如同《白塔之光》中的每個(gè)人。
盡管文慧帶給谷文通的是積極,是勸他勇敢地重新找回自己的父親,重新建立起聯(lián)系,但文慧自身卻很茫然。她是一個(gè)孤兒,一個(gè)向回看一片空白的人,她跟谷文通一起追尋過(guò)去,谷文通有一個(gè)真實(shí)可尋的父親就在回憶的那頭,但相同遙遠(yuǎn)的距離那邊,沒有一個(gè)人在等待著文慧。
很多觀眾會(huì)覺得,最后文慧突兀地就選擇了那個(gè)影片中鮮有露面幾乎存活在對(duì)話中的“前男友”,有點(diǎn)草率。

黃堯
“正是因?yàn)槲幕叟c谷文通有了這么一次尋找過(guò)往小小旅程,她才突然意識(shí)到自己想要抓住生命中唯一的確定,與自己根源糾纏的「東西」,也就是所謂的「前男友」,這個(gè)與歐陽(yáng)文慧一樣在孤兒院中長(zhǎng)大的孤兒。”黃堯講到,“我覺得他是文慧生活中唯一能抓住,屬于自己過(guò)往的把手。她割舍不掉。”
該如何定義孤獨(dú)呢?黃堯眼中的文慧,或許終其一生都在尋找影子,她的影子也許就是在北戴河,就是在那個(gè)人身上,那個(gè)前面從未提及的,最后突然冒出來(lái)的人身上。這個(gè)很像文慧的影子一樣的人身上。這個(gè)人可以是她的前男友,也可以是其他的什么人,這只是一個(gè)她自己的一個(gè)影射,或者她熟悉的有安全感的過(guò)去。

黃堯
誰(shuí)鑄造了「共情力」
黃堯的底色卻與歐陽(yáng)文慧截然不同。
如果說(shuō)文慧終其一生都在一種悲傷中度過(guò),在悲傷中企圖抓住另一份惺惺相惜的悲傷,對(duì)于世界有種天然的「不信任」;那么對(duì)于世界抱以「信任」黃堯的確相差甚遠(yuǎn)。家庭健全幸福快樂,除了職業(yè)路上遇到的正常起伏以外,沒受到過(guò)什么「令人唏噓」的重創(chuàng)。她自己也曾有過(guò)思索“我是不是成長(zhǎng)得太順利了?還是我的生活太過(guò)寡淡?是不是應(yīng)該更豐富一些?是不是要經(jīng)歷更多的事情?”
如果沒有感同身受,能夠演好這個(gè)角色嗎?顯然,黃堯摸索出了另一條成功的路。
孤兒,對(duì)于絕大多數(shù)演員而言很難復(fù)刻,“所以其實(shí)我能做的準(zhǔn)備更多的是對(duì)導(dǎo)演的,去了解導(dǎo)演的風(fēng)格,創(chuàng)作意向。張律導(dǎo)演很喜歡空間感,喜歡將人物放置在某一個(gè)空間里,去塑造TA的各方形象,我就要把我自己放進(jìn)他所創(chuàng)造的那個(gè)空間里。”黃堯說(shuō)道,“我沒有辦法一開始就想到想了一個(gè)很具體的人物形象在那,我只能是在創(chuàng)作的過(guò)程中,在舉手投足間變得越來(lái)越像她,思維越來(lái)越像她。”類似繪畫藝術(shù)中,通過(guò)塑造環(huán)境,將主體物的外輪廓勾勒出來(lá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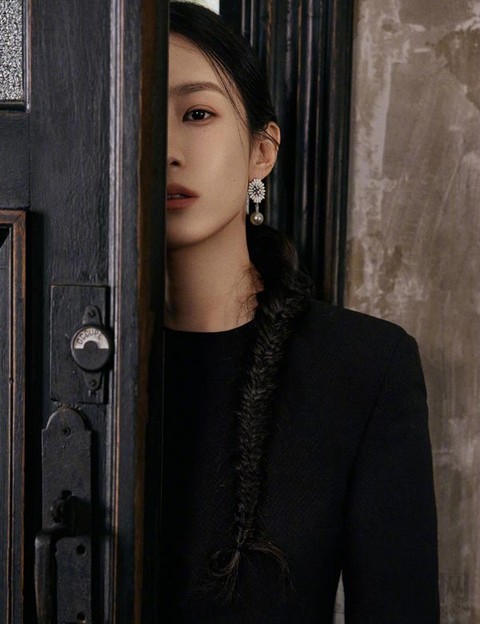
黃堯
共情力不一定只能來(lái)自親身經(jīng)歷,幸福和快樂也是一種情緒能力,能感知陽(yáng)光的人同樣有能力去體會(huì)黑暗。
七年里,她的演藝生涯、個(gè)人選擇、地域轉(zhuǎn)換,如同一塊沉淀豐富、分層清晰的巖石一樣,記錄和映射了不同的風(fēng)土人情和氣味鏡像,正是因?yàn)檫@種跨空間的接續(xù)性,黃堯的影迷廣大而松散。或許正是因?yàn)殪`氣、個(gè)性、自我、敏銳、悟性、智慧都會(huì)通過(guò)表情來(lái)傳遞,在她飾演的角色中總是混合起人格、聲音、表達(dá)、氣場(chǎng)、心性和演繹意識(shí),形成獨(dú)一無(wú)二的黃堯。逐漸增多的作品和反差較大的人物形象,使得她的觀眾有增無(wú)減。許多年輕人通過(guò)觀看紀(jì)實(shí)片、文藝片進(jìn)行自我學(xué)習(xí)和社會(huì)反思,不斷加入到她的粉絲群體中。
她的個(gè)性,她的演技,她的內(nèi)心。她懂得博取眾長(zhǎng),為我所用。
苦難并非唯一的共情力量,“天天高興也不妨礙我成為一個(gè)藝術(shù)家”。

黃堯
一個(gè)個(gè)「具象」抽象成「符號(hào)」
其實(shí)我們每一個(gè)人都是生活在符號(hào)般的城市中,一個(gè)小小的符號(hào)。
《白塔之光》講的是一個(gè)發(fā)生在北京的故事,與北京或許無(wú)關(guān),這僅僅是一個(gè)發(fā)生在有很濃的文化底蘊(yùn)以及人文色彩的城市的故事,這樣有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碰撞的地方,比較適合「追尋」。
后來(lái)黃堯沒有再特意去過(guò)白塔,只是有過(guò)幾次偶爾的路過(guò)。她說(shuō),白塔也許能代表一些人心中的北京。一提白塔會(huì)想起來(lái)北京,但反之未必。每個(gè)人我覺得對(duì)一個(gè)城市有眷戀,一定都是某樣?xùn)|西,某樣牽絆住他們的東西。這樣?xùn)|西也就變成了一個(gè)代表了特殊感情的符號(hào)。如同演員與角色之間的相互依存。
黃堯曾在采訪證講起過(guò),挺怕自己上了綜藝之后,會(huì)被大家記住本身的自已,從而再看什么角色都像是在看黃堯。
「這個(gè)時(shí)代改變了。互聯(lián)網(wǎng)碎片化時(shí)代,一切都是高效的、透明的,已經(jīng)不能讓我們?nèi)撕腿酥g產(chǎn)生神秘感。」

黃堯
粉絲文化在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tái)的橫沖直撞,不僅讓大部分普通用戶生活在全面的管控和規(guī)訓(xùn)之下,也讓生長(zhǎng)明星的土壤變得日益板結(jié)和貧瘠。也因此,黃堯的隨性和安逸顯得愈發(fā)的復(fù)古和「不合時(shí)宜」。
“我是INFP人格,內(nèi)心世界很大,當(dāng)然會(huì)很敏感,社恐也是常態(tài)。以前社恐的時(shí)候感覺自己非常的愚蠢,大腦一片空白。后來(lái)就接受了這樣的自己。以前很擰巴,刻意要改變,比如逼迫自己趕緊跟人熟悉起來(lái),進(jìn)行一些社交;但是現(xiàn)在就不會(huì)在心里強(qiáng)化自己一個(gè)性格標(biāo)簽了。自洽很多,覺得舒服的話我就去說(shuō)話,沒什么可說(shuō)的,那我就靜靜的待著,也不會(huì)不自在。”
雖然黃堯直到現(xiàn)在還會(huì)在意外界對(duì)自己的評(píng)價(jià):“對(duì)我的一些評(píng)價(jià)或者是一些專業(yè)上的表演上的一些評(píng)價(jià),如果是好的,我會(huì)覺得真的有這么好嗎?如果是不好,我會(huì)覺得他說(shuō)的好對(duì),會(huì)放大那些東西。”不過(guò)那些也都在不斷的自我重塑中被逐漸邊緣化。
后來(lái)的黃堯也不會(huì)再?gòu)?qiáng)調(diào)自己是一個(gè)I人,只是偶爾被問及時(shí)會(huì)如是說(shuō),就像偶爾路過(guò)的白塔,于是這些具象形容,逐漸蛻成個(gè)個(gè)符號(hào)。

黃堯
注定要是一個(gè)人
當(dāng)「精神內(nèi)耗」成為一種時(shí)代病,我們是否可以有所超拔,而非耽溺于它?畢竟,這種內(nèi)耗經(jīng)常以精致、優(yōu)雅、「文藝」的面貌出現(xiàn)。
歐陽(yáng)文慧與谷文通在北戴河,看著已成廢墟的爛尾樓,掩蓋了昔年擁有的一切,在一片暗色調(diào)的世界里傾軋而來(lái)的是甚至有形的悲傷。文慧俯下身,觸摸著她看到的一朵小花。
那一刻她不是文慧,她是黃堯。“有一朵小花在那支棱著。”黃堯說(shuō),“盡管你的過(guò)往可能是一片廢墟,盡管你覺得你的人生可能也沒有什么希望,但是你還是活著,生命還在那里。”還不算太壞,還有希望。

黃堯
很多人都說(shuō),黃堯自己也這樣認(rèn)為,一個(gè)人最好能找到自己的核心,這樣無(wú)論身處怎樣的境地,無(wú)論面臨怎樣的孤獨(dú)或苦難,都有力量度過(guò)去。那所謂的「核心」是什么呢?大概是某種堅(jiān)信,堅(jiān)信自己始終值得被愛,堅(jiān)信這個(gè)世界上有值得為之努力的事情。
同樣的,接受「一個(gè)人」。“盡管人跟人不停的發(fā)生交集,可是人的本質(zhì)還是孤獨(dú),但還是會(huì)有不停的有人走進(jìn)你的生命中跟你發(fā)生交集,這是一個(gè)很辯證的一個(gè)關(guān)系吧,所以不要害怕孤獨(dú)。”這一刻,仿佛聽到的既是文慧,又是黃堯,“或者說(shuō),感受過(guò)孤獨(dú)之后,才更加珍惜有人陪伴,有人跟你一起共度時(shí)光。”
在老北京的白塔開始拍攝的日子里,他們就像每個(gè)城市里充斥著為數(shù)最多的種類——上班族一樣,按點(diǎn)上班、下班,收工后彼此打個(gè)招呼,就在胡同口四散開去,混入車水馬龍和人群里。冬天的北京一路上風(fēng)吹得很急,黃堯也曾在北風(fēng)中騎得很慢,站在縱橫交錯(cuò)的路口目眩神迷,卻永遠(yuǎn)無(wú)法后退。于是她繼續(xù)計(jì)劃著前方,思慮著后方,選擇走一段體力恰好能承受的,又能盡可能多地看到美景的路。她有時(shí)會(huì)停下來(lái),看看被風(fēng)吹得些許狼狽的自己,稍稍整理凌亂的頭發(fā),就又要啟程趕路了。
監(jiān)制:佟宇 / 策劃:李祺 / 攝影:成沖 / 撰文:Linck / 妝發(fā):小敏 / 服裝造型:馬敏倩 / 助理:王宇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