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臧坤坤
看哪,這人
今天,做一個藝術家很難,做一個不甘平庸的藝術家更難。因為和藝術有關的所有東西,都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當再現成為問題,當主體的穩定性遭到質疑,沒有一個清醒的藝術家會坦然地背過身去,包括臧坤坤。
“難道我們今天還能畫《溪山行旅圖》和巴內特·紐曼(Barnett Newman)嗎?”顯然,這一發問表示,藝術在臧坤坤那里沒有變成一樁自戀的事業,他也不會僅僅在狹義的視覺或看著很時髦的意義上進行創作。問題意識源自清醒的判斷 :傳統的詩情畫意時代已走向終結,神秘主義傾向也已宣告破產,前人的創作實踐和他們的自我文化相契合,今天的藝術家亟須發明一種呼應當下的美學。
縱觀臧坤坤始自 2008 年的創作,表面上看是不拘一格、分叉開花,實際上內含一條隱秘的線索。這線索是人的形象,是主體形象的變遷。
一個經受過學院訓練的職業藝術家,能在創作之初就生產出沒有根基的圖案和沒有所指的形狀?如果這不是臧坤坤極力反對的“僵尸形式主義”,那么它意指何為?
臧坤坤在早期的繪畫里創造了一個個超現實的劇場,各種奇特的元素被組裝在同一個畫面空間,頗有“雨傘和縫紉機在解剖臺上相遇”的效果。不論這種手法借鑒自哪里,被制造的一場場異質性狂歡都毫無疑問地顯示出?一個青年藝術家的革命沖動和創造活力。
2010 年底,臧坤坤個展《現實的弧度》在北京林大藝術中心開幕。諸多觀者被他那種窮盡想象力營造空間場景以講述寓言故事的魅力吸引,但在一定程度上卻忽略了其中所蘊含的生命能量。在 2009-2010 年創作的《潛能》里,一個和尚將全身之力集中在一個手指的指尖上,空間是抽象的,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但臧坤坤讓人們看到,人面對無限也并非輕浮地存活于世。我倒立故我在,這是一種主體的自信。
臧坤坤的創作轉向是迅速的。沒過幾年,他就推出了“健身器材”系列。2011-2019 年間,他在這個系列上傾注了大量心力,鍍金、平涂、鏤空、肢解、圣像化等都是他采用的手段。如果說早期的超現實劇場展示出作為主體的藝術家瓦解既存秩序的努力,那么此刻,其實踐有了更現實、更具體的抓手。
尼采在《權力意志》里寫道 :“這個世界是,一個力的怪物,無始無終。”“這是權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皆無!你們自身也是權力意志?此外一切皆無!”無疑,臧坤坤充滿生命能量的主體在此遭遇到迎面而來的某種規范化的力量。
于是在這個系列漸趨成熟的過程中,人呈現出了相反的運動態勢,不是《潛能》里那種絕對自信的姿態,也并非強健、有力和充盈的,而是虛弱的、沉默的、無能為力的和逐漸消失的。

臧坤坤
現實的眩暈
如果給健身器材鍍金、把廉價的東西包裝成圣物以制造一種批判性效果的話,那么在稍后的“容器”系列和“海報”系列中,赤條條的垃圾箱和廣告牌則完全失去了這種意味。庸常瑣碎的物、羅斯科或者紐曼的畫、怪異的造型和結構…… 臧坤坤更大膽地使用挪用、拼貼等手法,卻對圖像保持一種冷漠的嘲諷態度。
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說 :“嘲諷是現代世界僅有的精神形式,這個世界把其他的精神形式都消滅了,只有它是秘密的獲得者。”這個世界不再神圣,藝術家在拒絕被收買和管理的同時,主動選擇成為一面鏡子,要使世界復歸無情的幻覺,恢復其不確定性。
在這個意義上,臧坤坤作為一個意識到世界之“擬真”性的藝術家,重訪了安迪 · 沃霍爾,他在實踐中將再次確認沃霍爾所確認的東西 :這個世界既不是具象的,也不是非具象的,它是神話式的。
垃圾桶是神話,所謂“崇高”的繪畫也是神話,它們也許曾經屬于不同的意義系統,但當它們在臧坤坤的畫面中相遇時,是落在了一個徹底冷漠的背景上,此刻的參照系是空。藝術家從創造性的行為中撤離,他只提供給人們純粹的圖像。
因此,你不必懷疑《巴內特 · 紐曼在中國(VII)》里的垃圾桶、紐曼的畫、美分硬幣,這三者之間不是一種平等的關系 ;《馬克 · 羅斯科在中國(III)》這件作品中包含的等比例的羅斯科繪畫、寫實的共享單車、不銹鋼反射的環境和藝術家的影子等等,都是被其“石化”了的嘲諷,是來自對象的幻滅。
在《容器,暗面》和《容器,應形》這兩件作品中,藝術家采用寫實手法描繪了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廣告牌,并保留了畫面的透視結構和縱深感,這樣的廣告牌可能也會和羅斯科或紐曼的畫作一起出現在其他作品中,但在這里,畫布兩邊的不銹鋼立柱和不銹鋼圓球不僅豐富著作品的結構形式,更造成了一種自我指涉的效果。
最終,一切形象都是鏡子,一切鏡子都在反射。所有形象都被巧妙或粗暴地剝奪了特殊性,以此向秩序提出了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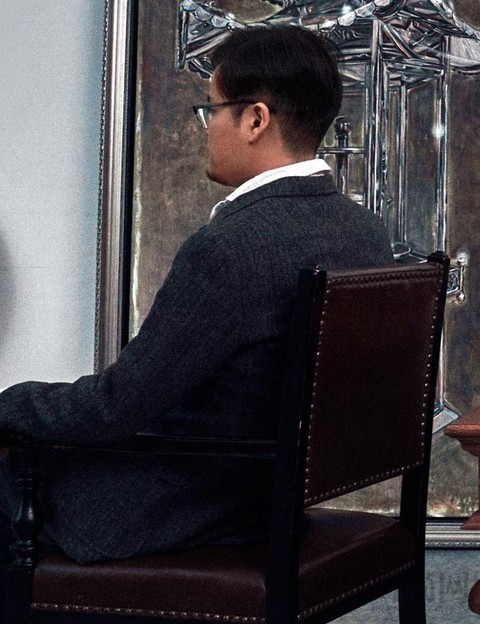
臧坤坤
藝術,另一種真實
臧坤坤說 :“好像繪畫才是屬于我的現實,真正的現實反而成了第二現實。對于外人來說,這可能顯得十分虛幻,但我知道它擲地有聲。”
在這個形象的生產鋪天蓋地、繪畫變得越來越邊緣的時代,臧坤坤的選擇乍看起來似乎顯得有些吊詭,但這絕不是屈從于繪畫的懷舊魅力,而是一種神話學之后的實踐。
首先,繪畫語言總是以遙遠的熟悉性牽扯著藝術家的求新欲望,這是他掙脫不掉的地平線。從美院畢業到現在,十幾年間,臧坤坤以不高產的創作狀態構思和雕琢作品,同時在更深的層面上關照著世界,并從未與世界脫節。他用一種幽默而理性、開放而嚴謹的態度改變著繪畫、雕塑等傳統媒介的工作方式,探索著藝術的邊界。
從早期的超現實劇場到“海報”系列,臧坤坤有意識地完善著自己的藝術生態。然后它真的漸漸長成了一棵樹的形狀,從根部開始長成了一個整體,每個支脈都是一個序列。每一個作品序列都在擴充著藝術語言的可能性,在語言之中求索,在藝術史的遺跡中嘗試、擴張和冒險,恰恰是對歷史處境的表達。
2020 年底,臧坤坤在瑞士蘇黎世 Mai 36 畫廊舉辦了名為“重屏”的第二次個展,“屏”在漢語中有“遮蔽”或“遮擋”之義,“重屏”則是兩層遮蔽的意思。整個展覽幾乎就是藝術家提出的一個雙重否定的諷刺說法,所有東西都在通貨膨脹中變得乏味,它們看起來相互對立,或者相互覬覦,但實際上什么也沒有發生,只是混亂。
在《流亡者的對話》中,德國戲劇家貝爾托 · 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描寫了兩個過境流亡者在火車站餐廳面對一杯啤酒的對話,齊費(Ziffer)說 :“這杯啤酒算不得啤酒。不過,它被這支雪茄也算不得一支雪茄這件事所平衡。如果剛才那啤酒不是一杯啤酒,而這雪茄卻是一支雪茄,那么一切都會不正常。”好像存在一架精巧的天平,垃圾箱也許是紐曼的對等物也說不定 :這就是藝術家對世界的想象。
總之,這個世界不需要通過抒情而被重新美學化,如今的先鋒藝術家更需要充分警惕媚俗的可能性。挪用、拼貼有時被狡猾而裝腔作勢的人利用,被他們當作通往市場的通行證。不過,沿著主體的消失、審美的幻滅這條路,人們反倒能看得出來臧坤坤是個例外。
策劃:齊超 / 攝影:程文 / 編輯、采訪、文:尚崢妍